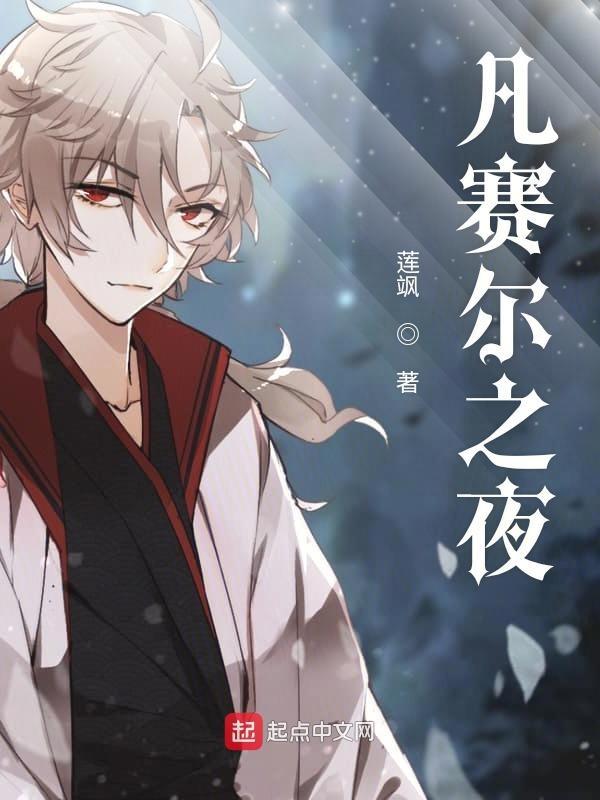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深恩不负全文免费阅读 > 第250章(第1页)
第250章(第1页)
难怪祝予怀一直都没来过信。
这么要紧的事,竟没一个人传讯告诉他!
卫听澜咬了咬牙,把岳潭往后一推:“回头再跟你算帐!”
他转头便往慈幼堂去了。
天光渐亮,伤兵营中四处都点了驱病避邪的草药。
营帐内,祝予怀从头到脚裹得严实,用竹镊掀起病患的衣裳,小心地查看疮口。卫听澜也用布蒙了口鼻,拿着一束点燃的艾草,焦急地在门口徘徊张望。
祝予怀看完病人,退出了营帐,卫听澜赶紧拉着他往远处走,也不管有没有用,先拿艾草往他身上来回熏。
祝予怀呛了呛,拦住他道:“别紧张,我没碰到病人,没那么容易传上。”
卫听澜更担心了:“当真是会传人的病?能治吗?”
“这是虏热疮,发现得早,能治。让没患病的百姓焚烧苍术、白芷、艾草,避开虫蛇,也能有效预防。最大的问题是,城中这么多人,药材不一定够。”
卫听澜一听有防治的办法,才稍微安心些:“药材好说,让岳潭想办法筹。泾水贪污案已经审完了,现在国库充盈,不缺这点钱。”
两人没有耽搁,换下衣袍出了伤兵营,卫听澜命人将祝予怀口述的药方记下来,抓紧送去给岳潭,自己则坚持要送祝予怀回慈幼堂。
祝予怀欲言又止,提醒道:“这疫病倘若是细作放出来的,他们为了避难自保,现在应当会着急出城。你不去城门盯着吗?”
卫听澜摇头:“城门已经戒严,细作狡猾,定有别的出城密道。既然防不住,索性让他们逃,雪山脚下提前设了埋伏,到时候我带人合围包抄,也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”
祝予怀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:“你要走了?”
卫听澜拢着他的手:“放心,我会尽快回来的。”
他将祝予怀一路护送到义塾门口,再三叮嘱:“疫病的事自有人操劳,你大病初愈,千万别累着。”
祝予怀愣了愣,才明白他今天这紧张兮兮的模样是怎么回事,不禁失笑:“我没生病,只是多睡了些时日,早养好了。”
前尘旧事,他并未遗忘,只是梦醒之时,他就已经看开了。
天道垂怜,给了他重获新生的机会,他若沉湎于前世的苦难,就是对此生的辜负。
祝予怀没有多谈,只把卫听澜往外推了推,笑着劝说道:“正事要紧,别耽搁了。你若是牵挂我,那就早些忙完,早些回来。”
他这么一劝,卫听澜也就只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。
祝予怀送走了他,独自回了义塾,时辰尚早,学堂里空无一人,易鸣和德音也去早市采买了,祝予怀无事可做,准备回屋歇一会儿。
他走到简舍门前,要推门时却又顿了顿,总觉得哪里不对。
他只迟疑了一瞬,房门就突然从内而开,一道黑影飞扑出来。祝予怀悚然一惊,转身想逃,却被死死捂住了口鼻。
一股浓烈的药味侵入鼻腔,祝予怀拼命挣扎,想抬手拔竹簪,又被那人钳制了臂膀。
迷药起了效,他浑身使不上力,正在这时,前院传来聂金枝直爽的笑声:“阿音,你说句公道话,今日要不是我好心帮忙,你二哥得被奸商坑掉底裤吧?”
易鸣似乎骂了句“女土匪”,聂金枝又笑着朝后院喊:“祝郎君,出来评评理啊,你这傻弟弟吃了大亏,还跟我别劲儿呢!”
几人吵吵闹闹,声音越来越近,祝予怀却无法出声求救。
他被人强行拖到了墙角,挟持他的人身手敏捷,扛着他爬上了矮墙。
祝予怀眼前发黑,拼着最后一点力气,摸到腰间的玉韘,狠狠扯了下来。
系着红穗的玉韘掉落在地,滚了几圈才停下。
聂金枝穿过了学堂,吊儿郎当地踏进后院,下意识停了步。
“聂金枝!”易鸣追了上来,生气地把她往回拽,“你这是私闯民宅知不知道?”
“等一下,”聂金枝皱眉望向院角的矮墙,“我刚才好像听到墙头有声音……”
易鸣恼了:“你又想耍谁?”
“你先别吵。”聂金枝忽然按住了他,“哎,你瞧那墙边地上,那个拴着红穗子的,像不像你大哥的玉坠子?”
易鸣回头看去,一眼瞥见墙角醒目的玉韘,神情这才变了。
卫听澜点完了人,刚准备出城,就收到了祝予怀失踪的消息。
“人是在义塾里丢的。”岳潭策马疾行赶来,气还没喘匀,先将一枚玉韘交给了他,“祝郎君的护卫发现异样之后,立刻就去追了,但没追上。湍城现在全城戒严,没人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事,我怀疑是瓦丹细作动的手。”
卫听澜攥着这系绳断裂的玉韘,指节都快泛了青:“他们想做什么?”
他前脚刚走,他们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人?
“你先冷静,”岳潭看他脸色极差,试图劝说,“他们没有直接杀人,而是将人带走,就说明祝郎君对他们有用……”
卫听澜根本冷静不了:“距离他失踪过去多久了?”
岳潭估算道:“将近一个时辰。”
一个时辰都没找到踪迹,细作没准都出城了。
卫听澜几乎咬牙切齿:“给青丝阙传急报,把陷阵营全部调回来,到雪山与我汇合。焦奕,候跃,立刻带人跟我出城!”
岳潭吃了一惊:“你要做什么?”
卫听澜将玉韘收进怀里,转身上了马,神情是前所未有的阴狠:“九隅要是回不来,我就带着陷阵营踏平雪山,灭了这帮畜生的老巢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