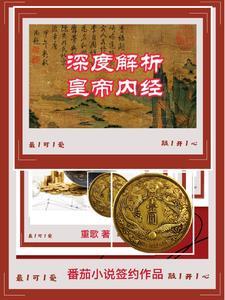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万年孤独馆在哪 > 第54章(第1页)
第54章(第1页)
这一点点的动静,使侍卫都看向了她,猩红双眼目不离视,头在脖子上打转,头转了一圈后,吭哧吭哧作响,像是狗爪刮动石子的声响。
阴君山嘴唇泛白,她看准时机拉着扶桑跑出去,但跑到了侍卫最前排的停脚处,他们的头就一个一个掉下来,滚到扶桑脚边停了一会儿,又滚走了。
这可把扶桑吓够呛,她脚踩着自己脚,饶是长成帝君看到如此奇怪的景象也会被吓到,更别说这两位被吓到腿软。
头咕噜咕噜滚,滚到后脑勺又滚回到正脸,张开嘴巴咯咯咯的笑,上齿碰到下齿,这声音比磨牙还要刺耳。
“长命锁碎,长明灯灭,人鱼烛燃。”
女声如支离破碎的莺啼传入耳中,侍卫的身躯如腐朽的树根碎成细渣,阴君山拽着扶桑在长廊狂奔起来,她们不敢停步,因为肉块追在后面。
就在转角处,阴君山撞上了一个人,一个站在廊间吹风的“白发”老人,她背对着她们,等她转身后,只见一对灵动活力的眼睛。
她是个年轻人,嘴里嘀咕着一些诗,轻声道:“白发苍苍竹林站,遥看似鹤似白玉。”
扶桑在女人念诗时,回头看,肉块停止了追逐,它在原地不动,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女人讲完诗,再开始慢慢,慢慢地蠕动。
女人身披白羽衣,面带由白玉做成月牙装一次排下到下巴的面具,一双白色眼睛,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,她对两人歪头笑笑,直径走向肉块,蹲下温柔道:“好了,乖宝宝,躺回你的床上吧,天黑要睡觉了。”
肉团极其听话,它一鼓动一鼓动地爬行,渐行渐远地爬向远处。
阴君山长叹一口气,她回头望着女人,迟迟没开口,等四处寂静,无婴啼鸟鸣,她迟迟开口道:“你是谁?”
“……”
女人流白的眼睛看不出任何情感,她双手在空中舞动起,如同在月光下飞舞的蝴蝶,她眯起眼睛,指节停靠着一只蓝黑蝴蝶,那是她身上唯一的色彩。
她轻轻说:“今晚月色真美。”
只有一句话,女人同风消散,在月光下无影无踪,如昙花一现,也如月光一刹。
阴君山望天,月亮消散,初阳乍现,她看天再望着天,天要凉了。
趁着天没有很亮,她们赶回了阴家,也就是那个时候阴君山再次遇到了那名女子,她打心底的怕意已经将她和肉块分成一类了。
女子正在和梅林说话,她的样子看起来极冷漠,也有些许的不耐烦,她张嘴闭嘴只说了半句话,发现了阴君山,眨巴着眼睛又闭上。
阴君山闭上眼睛又睁开,女子不见了,她再闭上眼睛睁开,女子出现在她眼前,一双白到透光的手捧起她的脸,问:“晚山,你有听到什么吗?”
晚山,你有听到什么吗?
这句话来来回回在阴君山脑子里重复了十几遍,她想为什么女子会知道她的名字,那女子和梅林是什么关系?
很快就有了答案,女子贴在耳边,轻声细语道:“因为我认识你,我和梅林是母子哦。”
母子,真是一对奇怪的母子,哪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孩子偷渡到这里来,穿过一片海水来到这里?
女子抿唇,显然从阴君山眼神中看到了质疑,她指指远处的梅林说:“你瞧,他坐在那像不像我。”
“不像。”
女子哽咽一下,继续说:“那你去问问他好啦。”
阴君山听话地点点头,走到梅林轮椅前,蹲下附在耳边说了什么,气的他要站起来打人,许是劫后余生的轻松让阴君山笑起来。
女子颇为满意的看着两人,坐在长廊上垂下腿,面前是一汪池水,她低下头睁眼闭眼间,一双流露白霜的眼睛变得湛蓝,再闭眼睁眼,又是白色的眼珠,水面干净透亮,倒映出她只见眼睛的脸。
过了很久,天亮了。
阴君山静静听梅林说,说阴芙给他讲了很多故事,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,天亮了,她垂下头温柔地笑,梅林看到笑愣住,这个画面在他脑海中,千遍万遍地流淌过。
今日是扶桑节,挨家挨户挂红灯笼,阴母早起做了晨饭,又爬梯子挂灯笼,扶桑自回来去屋中睡了一个时辰,爬起来看天微亮,继续倒头再睡一会儿。
直至天黑,她才从睡梦中醒来。
她撑起身子,明月挂于天边,近在咫尺又远在边,扶桑穿好衣裳出屋,院子内没人,她推开门见到急冲冲赶来的许池鱼,问:“人呢,人都去哪了?”
“坏了,坏了!”
这句话过后,扶桑跟着她跑在街上。
扶桑节是庆祝扶桑出生而独设的节日,扶桑花与丧服极其相似,又有死人花的别称,这天会有格外多的鬼魂,又称鬼节。
魂魄若被破坏,再入轮回则为痴儿,这天会有阴差保送,要是在这天闹事,关系重大问题,是要被判十八层地狱。
推开人群,扶桑看到了昨日夜里的那团触手,它正在疯狂的啃食魂魄,而阴君山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把剑,对着触手砍,也只是砍下来两三根在地上蠕动,接着又爬回本体。
阴差察觉不对,严令魂魄往回退,一大队呜呜泱泱的魂魄,像一片黑压压的云退出街道。
扶桑从旁边摊子上摔碎一个茶盏,用碎片割破手腕,鲜红的血液从伤口流出,她又用另一个茶盏接血,接了满满一茶盏后,她把茶盏丢到触手上,真神血与邪触碰,一阵红光后,触手萎缩到一点点。
它仍然不死心的大喊起来,如婴孩啼哭。
“长明灯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