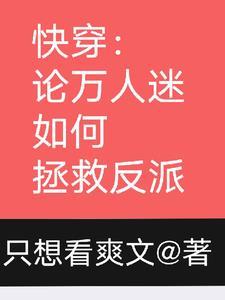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手握空间和离后开启流放高端局 > 第73章 纳妾(第1页)
第73章 纳妾(第1页)
傅灵蕊吃惊地张大了嘴巴,“啊?没有,我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什么?”袁诤迅打断了她的话,“你看看你,连管个家都管不好,天天就知道问问问。灵蕊,如果我什么都能管、什么都能做,我娶……我把你接进府有什么用?”
傅灵蕊眼圈泛红,用力咬了咬唇,轻声说道:“可是我留在府里,终究名不正言不顺,府里的下人也不把我当主子。我说得话,他们根本不听。”
她低下头,声若蚊蝇,“还有,府里的月例银子,拖了快一个月。金嬷嬷已经问了几次……”
再不,估计下人都得闹情绪了。
这府里的庶务,有银子谁不会做?
只要银子到位,什么话都好说。
又让管家,又不给银子,难不成这府里平日都是嗑空气?
袁诤一听,顿时头大如牛,“府里没银子了吗?上个月母亲不是才贴补了三千两银子?”
傅灵蕊小声道:“上次表哥在酒楼与人生争执,赔了一千两。”
袁诤瞬间想起来了。
半个月前,他在酒楼喝酒,听到楼下有人在说笑,言语中提到“拿妻子的嫁妆银子贴补外室”。
他当时喝得有点大,闻言顿时勃然大怒,从楼上冲下来,抡起凳子就将那人揍了一顿。
喝醉了下手无轻重,将那人的腿给打断了。
结果那人的同桌作证,人家压根说得就不是他。
而是一个岳家开书坊的秀才。
那人咬死不松口,扬言非要闹到陛下面前。
最后只能找了傅恪做中人,花了一千两银子才将此事私了。
让原本就不宽裕的伯府更加捉襟见肘。
袁诤只觉得头疼欲裂。
没银子,他就算想娶傅灵蕊,也拿不出聘礼来。
他必须尽快想办法,解决眼前的困境。
想到这里,他努力打起精神,转身朝怡心院走,“算了,我去见母亲。你先去……”
袁诤手指划了几下,指向月华院方向,“你先去月华院,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先把勇毅伯老夫人的寿宴应付过去。”
他往院门外走了几步,犹豫再三又倒回来,对傅灵蕊说道:“东哥儿和成哥儿启蒙的事,你要不,回去问问舅舅,看他那边,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?”
傅灵蕊便知袁诤让她回去的目的,是想让她在父亲面前,帮他问问差事。
在廖华裳离府的这一个多月,傅灵蕊越来越看不清袁诤的态度,心里越来越没底。
原来廖华裳在府里的时候,从不拿着当回事。
如今人走了,袁诤反而开始天天宿在月华院。
连碰都不碰她。
对娶她过门一事,更是只字不提。
她无名无份留在伯府,忍受着下人的轻慢和指指点点,劳心勠力为他们操持着庶务,到头来却只落了个“有什么用”。
可事到如今,她除了打落牙齿往肚里咽,还能有什么办法?
甚至乍一听闻袁诤吩咐她做事,傅灵蕊竟然还感觉很高兴。
至少说明,她对袁诤还是有用的。
傅灵蕊强忍着心里的雀跃,连忙答应下来。
可当她从傅府回来,看到的却是那位面如桃花、满脸羞涩的妾室周氏。
她不过才回去住了五天而已!
她为了袁诤的差事,忍受着父亲的冷脸、忍受着继母的嘲讽,还要忍受着兄弟姐妹的羞辱。
这些天她伏低做小、唾面自干,觍着脸留在傅府,就是为了能求得父亲同意,替袁诤在刑部尚书面前说句好话。
谁知,袁诤竟然又背着她纳了妾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