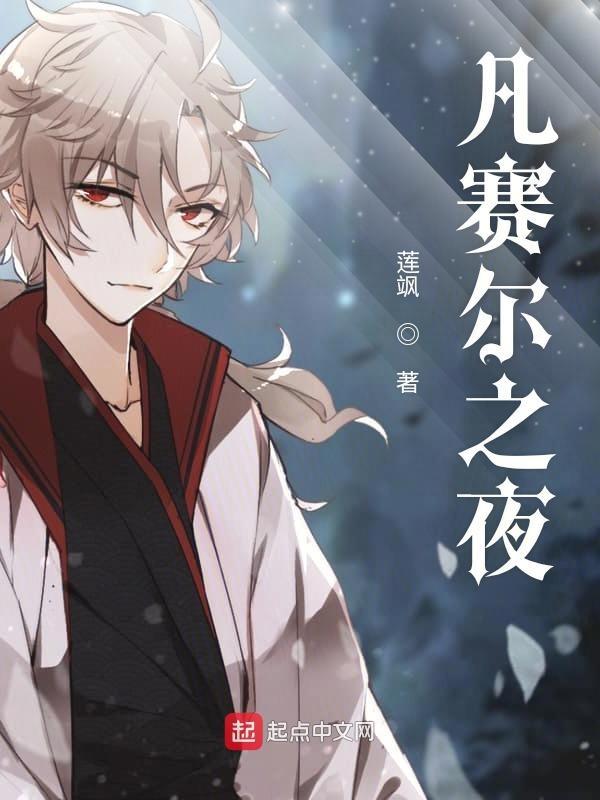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她不是潘金莲再枯荣全文免费阅读 > 19 烟雨暗〇一(第1页)
19 烟雨暗〇一(第1页)
西屏吩咐上茶,却不见如眉,因问红药,红药也不计较,笑说她在屋里睡觉。西屏面上就有些不好看,当着人没作,只轻声道:“叫她起来,有客呢。”
时修原要在榻上落座,一看南台只在左下凳上坐,他也不好太没规矩,自走去圆案旁坐,就着案上的冷茶,十分不客气地给自己倒了一盅,“三爷有什么事?”
南台倒有现成的话拿得出来搪塞,“我听李仵作说,现那尸的时候,是跪着的?我左右想不明白,若说跪地求饶,就不应当是被勒死的,人被勒着的时候,手乱抓,脚乱蹬,根本跪不住。”
时修搁下茶盅,凝着眉暗忖片刻,“你不说我险些忘了,是有些不寻常。她不是跪着给人勒死的,是尸被绑在那树上的时候,刻意摆出的这个姿势。”
“刻意?”西屏不由得打个冷颤,呷在嘴里的茶有点恶心起来。她吐在盂内,睃着二人道:“凶手为什么要多此一举,给她摆出这样的姿势?”
时修徐徐道:“下跪是一种臣服,认错的姿态,也许凶手是觉得那许玲珑有哪里对不住他。”
西屏马上想到与庄大官人相好的别的那些女人,“庄大官人说的那些女子,你怎么不去问一问?”
“午间去府衙就是为这事,我派臧班头去问了,只看他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。”
南台道:“能把个人活活勒死,我看凶手力道不小,不像是个女子所为。”
西屏微笑道:“妇人家也有天生力气大的,三叔不可一概而论。要勒死许玲珑那样一个荏弱女流,比她强些的女人也未必不能挣得过。”
南台便又改了口,“二嫂说得也有理。”
好像是有点故意附和西屏的意思,时修在旁不则一言,转过身去对着案,呷了口冷茶,眼梢斜着溜他一眼,又抱怨茶涩口。
“谁叫你急性吃它?那都是晨起沏的了。”西唤够着脑袋朝外间看,那如眉还没过来。又见南台殷勤地去给她倒了杯水搁在炕桌上,她轻轻谢了声,转叫时修,“你来,我看看你胳膊好些没有?”
时修却只管坐在那案旁不起身,“一点小伤有什么要紧,不值得看它。先时查案追凶也伤过几回,这还算伤的轻的哩。”
“净说大话。”西屏乜他一眼,鼓着点腮板下脸,“快过来我瞧瞧,再不要叫我说第三遍。”
又端长辈架子,他没奈何,懒懒地走到跟前,撸起袖子给她看。如今不扎棉布了,伤口结了一条粗长的痂,像一条可怖的蜈蚣。
西屏旁若无人地在那痂上碰一碰,“还疼不疼?”
其实明知南台就在一旁,就像有意要做给他看。有一年南台伤了脚踝,她也曾避开姜家众人,暗地里对他表示过关心,但他是怎么说来着?好一个循规蹈矩的姜南台,他那般义正言辞,无意中将她归类成个不知礼义廉耻的霪妇。
她当下摸着时修的伤疤,有种报复性的快意。
时修不觉得痛,只觉得痒,好像她摸过的地方在迫不及待地长着新肉。他把手垂下去,袖子也垂下去,不以为意的口气道:“我岂是那等脓包么,这点疼算什么?”
西屏偏笑他,“你这猫,休要嘴硬,那大夫给的药膏子记得叫丫头给你搽。”
他有些不能克制的柔情蜜意散在心里。
这一来一回对答间,将南台干晾得太久,他趁势插话,“划伤二爷的,可是那日抓的那个犯人?”
时修走回案旁道:“那是杀害许玲珑的疑凶,不过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”
西屏道:“勒死她的是一条蓝色绫子,脖子上的勒痕又粗,依我看,不一定是那庄大官人,想是庄大官人别的相好,女人间吃醋,不正有杀人之心?那条蓝色绫子也想是女人的披帛或是裙带,要不就是条汗巾子。”
时修一时反剪胳膊,又成了那知深睿达的小姚大人,“扎汗巾又不是只有女人,男人也扎得。”
西屏嗔他一眼,噘着嘴咕哝,“我又没说不是男人做的,我是说,女人也不能轻易开脱得掉。”
他走到跟前,故意歪下脑袋逗她,“那依您之见,那许月柳像不像凶手?我听说她和大姐许玲珑久来不睦,倒可以起杀人之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