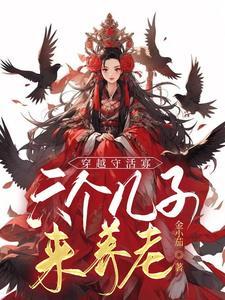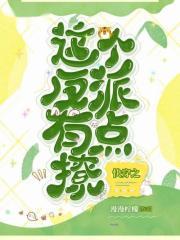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被洪水冲走的人变成什么样 > 突如其来的电话(第1页)
突如其来的电话(第1页)
“快到家了!”小禾指着半山腰一座稍大的窑洞,门前有棵老枣树,“枣子再过一个月就能吃了,可甜了!”
走进窑洞,江宁意现门框上贴着一张被擦拭的干干净净的“光荣之家”奖状,旁边挂着张家宝的军装照。照片前的小香炉里插着三支香,青烟缓缓上升。
张奶奶注意到江宁意的目光,轻声说:“每天早晚三炷香,让家宝知道家里好好的。”
窑洞内还算宽敞明亮。
土炕上铺着整洁的床单,墙上贴着几张日期连贯的奖状——都是小禾在学校得的。一张木桌上摆着简单的饭菜,还冒着热气。
“快坐下吃饭,走了这么远的路肯定饿了。”张奶奶招呼道,“没什么好菜,都是自家种的。”
饭菜并不简单——豆角烧肉,腌萝卜,玉米面馍馍,还有一小盆鸡蛋汤。
味道出奇的好,江宁意吃了两大碗。
“宁意姐姐,陆哥哥说您在西北修复文物?”小禾一边吃饭一边问,眼睛里满是好奇,“是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老古董?”
“也不算特别厉害,”江宁意笑着回答,“就是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器物。比如铜器、瓷器之类的。”
“小禾可喜欢听这些了,”张奶奶插话道,“上次你们寄来的那本带图的历史书,她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。”
晚饭后,小禾抢着洗碗,江宁意也去帮忙。窑洞外的水井旁,两个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女性很快熟络起来。
“宁意姐姐,西北是不是特别大?有没有十不,二十个长义村那么大?”小禾一边麻利地刷碗一边问。
江宁意被她的问题逗笑了:“比那还要大得多。有机会的话,你可以去看看。”
小禾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:“奶奶身体不好,我不能走太远而且”
她没说完,但江宁意明白了言下之意——经济条件不允许。
回到窑洞里,陆洋正在帮张奶奶修理漏雨的屋顶。他站在梯子上,动作熟练地铺着新茅草。
小禾在下面递工具,两人配合默契。
“小陆啊,别忙活了,下来喝口水。”张奶奶心疼地说,“大老远来一趟,净干活了。”
“马上就好,奶奶。”陆洋头也不回地答道,“趁天还没黑,我把围墙那裂缝也补补,万一下雨就麻烦了。”
江宁意仰头看着陆洋在夕阳下的剪影,小禾看他的崇拜眼神,张奶奶站在一旁欣慰的微笑。
这样的陆洋,是在军装和枪械之外的另一面,温柔而可靠。
夜幕降临后,长义村里还没有通电灯,只有煤油灯昏黄的光。
小禾端来一盆热水让客人洗脸洗脚,自己则坐在炕边,借着灯光翻看小学的课本。
村支书是在第二天清晨跑到了张奶奶家门口找陆洋。
军区的电话,一路波折终于追到了长义村。
陆洋听说是军区的电话时,愣了好一会。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,如果是按照他之前所在的世界,这个年代确实是爆了战争。
他奔跑去村社的路上,惊飞了门前枣树上的麻雀。江宁意正在院子里帮小禾打水,她看见陆洋开了门和支书说了两句话,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冲了出去。
“喂,我是陆洋。”他的声音瞬间变得严肃而紧绷。
村社里除了值班的乡亲,就是站在门口的支书。
“是,明白。我立刻返回。”陆洋简短地回答,随后挂断了电话。
陆洋放下电话,手指微微颤。
他的脸色显得格外苍白,值班的老李头递来一杯热水,他机械地接过,却忘了喝。
“陆同志,出啥事了?”村支书小心翼翼地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