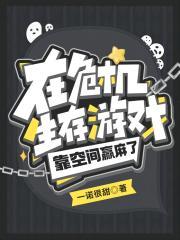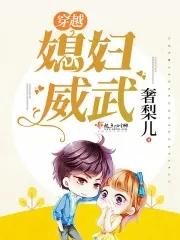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夫人要合离 > 第12章 阿兄(第1页)
第12章 阿兄(第1页)
江府花厅。
本应是愉悦的氛围却因为一位许久不见之人的加入,而倍感凝重。
丫鬟们忙着上菜,厅里只有瓷盆碰撞桌板的声响,混杂着丫鬟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。
江心白率先开口,试图打破这沉寂,“绾儿啊,凌……侯爷没有病的很严重吧,要紧不?”
江绾摇头,眼睛是看着江心白的,但余光却满是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
“偶感风寒,不严重,他本来身子骨就弱,就没办法陪我过来见你们,托我向你们赔个不是。”
“啊,这样啊,没事就好,早晚会见到的,咱不急,让他好好休息。”
“嗯。”
空气再度陷入凝滞,仿若要将花厅外飘散的雪僵在半空而不流动。
直到赵氏端着一小盅海带豆腐汤过来,放在江绾桌前,她关切的言语融化了氛围。
“绾儿啊,这是你最爱喝的汤,不是喜欢为娘做的吗,来,快尝尝。”
江绾眼含柔情,舀了一口入嘴,是熟悉的味道,这海带排骨汤,只有赵氏会放糖,暖胃又暖心。
江绾又喝了一口,眯起眼睛,有了笑意,“谢谢母亲,很好喝。”
赵氏期待的神情展开后是喜上眉梢,“就知道你馋这口,如今嫁做人妇,往后在家的日子就少了,趁着你回来,赶紧上锅,这口汤啊,为娘可熬了两个时辰。”
“辛苦母亲了,”过了会儿江绾才彻底将目光投向对面的人,“母亲,锅里还有剩吗?”
赵氏给她夹了口红烧肉,“自然有,够你喝的,不着急。”
“不是,”江绾又说:“给阿兄也盛一盅吧,阿兄昨日才回来,五年不归家,想必比我更想念母亲的手艺。”
此话一出,引得桌上的另外三人眼珠子互相瞟着。
江玉瑾夹菜的手一顿,望向自家亲妹妹的眼神先是讶异,而后是不解,再然后是隐忍的喜悦。
赵氏心里眼底充斥着意外和惊喜,毫不掩饰,忙吩咐下人,“是!当然要,快,快,允嬷嬷,给我乖儿子盛一盅上来。”
江心白松了口大气,不再郁结,刚才那氛围,分明在自己家里,却像是在跟大人们应酬。
话都不敢乱说。
他江绾夹了块牛肉,解释:“绾儿,你怎么知道你阿兄昨日回来的,这不,回来得急,为父都忘记给你捎个信了。”
江绾又喝了一口汤,笑容浅淡。
哪里是忘记了,分明是没打算说,毕竟自从那件事后,她与江玉瑾表面是有血缘连着,实则形同陌路。
那时她才十岁,性子与现在截然相反,活泼好动。
江玉瑾是她唯一的亲兄长,尽管平日少言寡语,但对她却是极宠爱的,不论爹娘在不在家,大多日子都是他在照看她。
那年上元佳节,江绾提着跟婢女一起做的灯笼去他院里的书阁找他,千磨万磨,让他陪着一起去逛街市,猜灯谜。
她阿兄猜灯谜是这一片里出了名的厉害,每次都能拿到最高最好看的那个灯笼。
可那会儿他正忙着,提笔坐在书案前写写停停,温声对她说:“你且等等,写完这个,阿兄就带你去。”
得了准信,江绾只好耐心等着。
提着灯笼,在他书阁里到处走,一会儿拿本书翻翻,一会用指尖划拉着系在竹卷上,垂在外边的标签,晃荡来晃荡去,百无聊赖。
见到一副被藏得很深的画,她想抽出来,却怎么都抽不动,她不信邪,再度用力,总算有了动静。
却因为手滑,再加上力的反作用,她不受控制地往后倒,灯笼被她放开,落入了旁侧的火盆中。
火光“哗”往上窜,冬日干燥,火星子没长眼,到处乱跳,没等人回神,就已经将四周的易燃物拖入火堆。
“啊!阿兄!阿兄!”
“阿兄!灯笼!灯……”
江绾受到刺激,哇地大哭,火势已经不受控制,江玉瑾顺着声音,捂着口鼻赶过来,将坐在地板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江绾抱起,冲了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