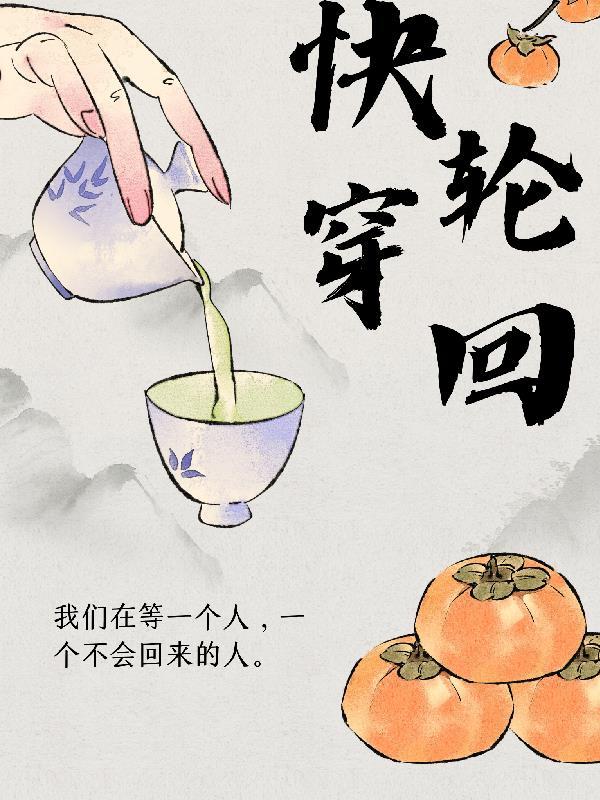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虫族上将 > 第98章 饴糖(第1页)
第98章 饴糖(第1页)
凌晨一点?,魏邈浏览完评论区,正要关闭光脑,便?听见门?口传来相当轻微的脚步声。
门?轻轻开合,几?乎没有发出?任何声音,灯泼洒下来,魏邈从衣柜里取出?一套崭新的睡衣,便?若有所感,抬起眼。
奥兰德站在门?口。
对方的装束依然是傍晚时的模样,只是脱掉了外套,肩宽腰窄,眼眸怔松、涣散地看着他,瞳孔有些失神,魏邈视线下移,定?格在他手里的那柄薄薄的刀上。
他没想到这个时间点?儿,雄虫竟然还没有睡觉。
“您怎么还没睡?”奥兰德的目光定?格在他脸上,过了半晌,才挤出?一个笑意,低声说,“雄主,我不是故意来打?扰您的。”
接触到魏邈的视线,他很快就如同被烫到一般,将刃尖向身后藏起,呼吸还略带急促。
恶人先告状。
冷不丁闯入他的房间,然后问他为什么还没睡?
魏邈神色如常地喝了一杯水,转身将柜门?关起,他唇色很淡,神色清清淡淡,眼眸的涟漪如同投进去一颗细小的石子,又很快的消匿不见。
他将眼镜随意地搁在桌子上,看了眼窗户的位置,觉得想要毫不费力地逃生,多少有点?儿够呛,问:“打?算动手了?”
奥兰德飞快地摇了摇头。
他情绪明?显有些不对劲,脑子里焦躁不安,各种?各样的情绪随时要将他吞噬。
他最近总在做梦。
各种?各样的梦,乱七八糟、毫无章法,场景随时变化,梦境里大多围绕着他的雄主,里面?有很多其他的虫,都要来抢他的位置。
那场精神力的疏导只是饮鸩止渴,一时的安心之后,反而让他更加焦躁、无序,雄虫的态度疏忽不定?,仿佛离他很近,但他难以揣测那份心的距离。
……要怎么样做,才能?复婚?
复婚。
脑海中的念头越来越清晰和强烈,只有雄虫绑在身边,他才会?有片刻的安定?。
去看他一眼。
雄主肯定?已经睡了,他悄无声息地过去,谁也不会?发现。
奥兰德这样对自己说。
雄虫身处在和他同层的卧室,离得相当近,他悄悄地走过去,迎接他的,却是满室的亮堂。
就连他的影子也在灯下无所遁形。
他不知道已经惹怒过雄主多少次,或许本?就没有伏低做小、讨好他的天?分。
他做什么都这么拙劣,被清楚得看在眼里,他不清楚雄虫知道多少,也不清楚这五年来,积累的裂缝已经大到了什么地步。
了解他了解得这么清楚,他的面?具就像是维恩的玩具,被随意地撕扯下来。
奥兰德也清楚自己的本?性有多么不讨喜。
……假如无法弥合呢?
他不敢想这个可能?性。
一想到雄虫会?彻底地不再爱他,滋生的冷意和暴戾就逼得他辗转反侧。
“我想到了一个让您解气的办法。”奥兰德已经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,慢慢地走近,低声说,“您捅我几?刀,消消气,好不好?”
那就换个更直接的方式。
他的雌父曾一度用这样的方式取悦过他的雄父,奥兰德当时冷眼旁观,觉得这是一出?颇有观赏价值的情景剧。
愚蠢、荒谬、费解,细思是一种?残忍。
卡里尔·柏布斯可笑得有点?儿过头,被金鱼绊住手脚之后,大脑就日益退化,觉得这样剑拔弩张的相处模式能?够依靠一张结婚证,便?长长久久的维系下去。
他的雌父甚至寄希望于他能?够让雄父回心转意,对他稍微优待一些。
奥兰德对此兴味索然。
让他去向那位脑浆晃匀了的雄虫讨巧卖乖、摇尾乞怜,无异于彻头彻尾的羞辱。
·
但他如今突然觉得,这未尝不是一种?解法。
他的身体?可以抗下这样的惩罚。
那柄刀足够小巧,也足够锋锐,恰好方便?雄虫单手握持,他的雄主很会?用刀,那或许是从第九区学来的技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