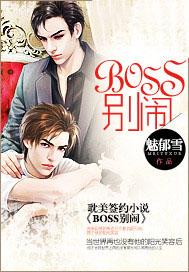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病弱女帝拯救中全文免费阅读 > 第65章(第2页)
第65章(第2页)
“我不要睡觉,我回来是替你诊脉的。”唐笙倾身,像是要枕在她膝上似的,“你发给我的折子上有血。御医也说你‘忧思深重,腹脏结愁’。”
她说着说着便忘记了敬称,秦玅观被她的眼眸攫取了注意根本没有觉察到,唐笙自己亦没有觉察到。
“晌午了,先用膳罢。”秦玅观道,“朕今日召你侍膳。”
唐笙抿唇笑,跟着秦玅观起身,往内殿去。
幽州治疫的这段时间,官差一体,自唐笙到差役,无论男女,吃的是同一锅饭,睡的都是门板架的榻,没人享有特权。秦玅观赏的这桌色香味俱全的膳食,看得唐笙是两眼泛光。
她用得香,连带着看她用膳的秦玅观也多进了些膳食。
“幽州是缺粮么?”秦玅观搁箸后忍不住问。
吃饱喝足的唐笙斯斯文文地擦拭嘴角:“暂不缺粮,但没御膳房的膳□□细,整日吃那些会腻。”
她这样一说,秦玅观便明白了。
从前她治军时也是这般。军中比县衙要苦,行军时莫说是新鲜滚烫的饭食了,就连吃饱有时都很难。
庆熙年间,同瓦格的最后一场仗,齐军断粮,她和黑水营的将士只能吃耐饥丸就着醋布煮成的糊糊,那味道,她现在想起来还会犯恶心。
宫中再怎样都比地方要好些,唐笙确实是吃苦了。秦玅观的视线描摹着她更显英挺的鼻梁,落于她线条流畅的下颌。
“苦么?”她问。
“不苦。”唐笙答,“为陛下做事,不觉苦楚。”
秦玅观不信,她屈掌,示意唐笙过来。
她在唐笙面前卷起衣袖,淡淡道:“把脉罢,瞧瞧朕到底是什么病。”
唐笙温热的指尖覆上她的腕子,轻轻搭在脉搏上。做这些时,秦玅观正饶有兴趣地打量她,像是要将她看穿了。
离得这样近,唐笙逃不过她的目光。她只能佯装不知道,面颊和耳朵却染上了红晕。
“陛下,您这是……”
“手怎么了。”秦玅观在她收手前捉住了她的指节,将她拉近。
唐笙下意识瑟缩,却被秦玅观使些力气拉了回来。
“朕命你摊开掌心。”秦玅观冷冷道。
唐笙内心挣扎了一会,终究是没敌过秦玅观目光,乖乖摊开了掌心。
那日握匕首所留下的创口缩成了长长一条疤痕。前些日子,她忙时顾不得这伤口,硬是拖了二十来日,创口才愈合。
“这是哪弄的?”
唐笙解释了一番,秦玅观久久不语。
秦玅观头一次清晰地打量这双手,是唐笙头次入殿值夜那次。
她折子批累了,被灯火晃了眼,还是小宫娥的唐笙蹑手蹑脚地捧来了灯罩,骨节分明的指头覆在光晕上,侍弄了许久的灯火都没卡对位置,微屈的指尖泛着白,压着一股劲。
秦玅观打心眼觉得这双有力量感的手很漂亮,而手的主人却很蠢。她忍了忍,终于探手替她摁下了灯罩。她的食指贴着唐笙的小指,一冷一热,对比明显。
而今这双手多了道深色的伤疤,瞧着就很痛。即便伤口愈合了,秦玅观不敢抚摸这道狰狞的疤,忧心唐笙会觉得痛。
“陛下——”唐笙唤他。
“颈上也是那次弄的么。”
秦玅观探出指尖,压下她的衣领,微凉的指腹抚着那片。
唐笙觉得很痒,但又舍不得躲开。
“一点皮外伤而已,不严重。”她低低道。
“皮外伤么?”秦玅观反问她,“除了受皮外伤,是不是还起了高热,感染了风寒?”
“是十八说的吗?”唐笙急需知道谁在给秦玅观告密。
秦玅观捏着她的脸颊,托起她的下巴。先前唐笙跪在脚踏边时,她就想这样了,可在佛祖面前她还是敛住了心绪,未敢造次,一直忍到了现在。
“陛下,我经受的这些不算什么。您挨过刀伤,趟过江水,没有闲暇,明明是在做利于社稷的事,却还要下罪己诏……同您吃过的苦头比起来,我经受的真不算什么。”唐笙被她捏得心跳加速,说话磕巴。
秦玅观俯身:“所以你觉得,能在幽州替朕多扛一些也是好的。”
她幽暗的眼眸里燃着微弱火光,唐笙在她的掌心轻巧颔首,唇瓣蹭到了她的指腹。
思念点燃了火焰,秦玅观像梦中那样,亲吻她的唇瓣。
唐笙乱了鼻息,但不忘以微弱的音量提醒秦玅观,她是从疫区回来的。
“亲都亲了,你说这些是不是晚了?”秦玅观笑得戏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