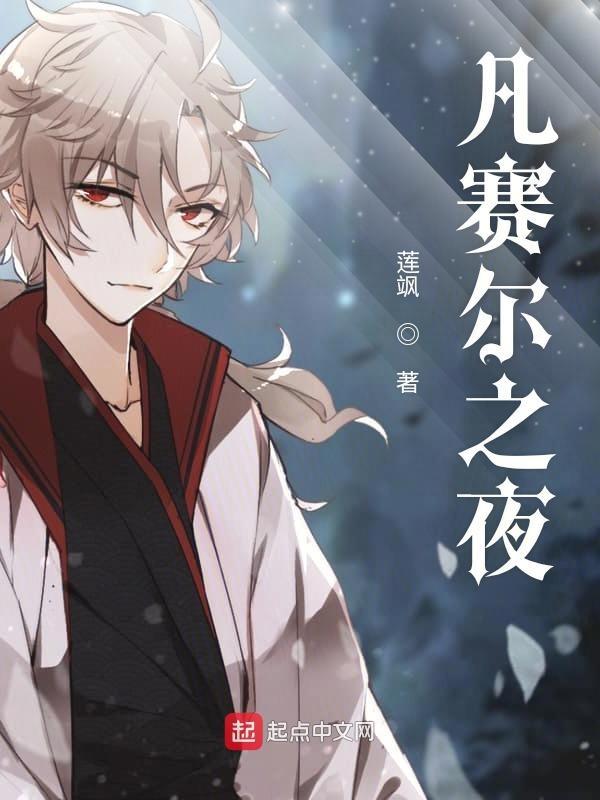紫夜小说>醉卧江山 > 第55章(第1页)
第55章(第1页)
谢明裳没什么?同情心地想,那可真活该。
萧挽风把?酒葫芦递给顾沛:“两边无意撞上,还是一方刻意堵人?”
亲卫也?说不上来。
搀扶萧挽风出宫的其中一名年轻内宦忽地开口?道:“奴婢知道一些。”
萧挽风看他一眼。年轻内宦上前两步,附耳低语:
“谢公今早上就?来啦。长跪在武定门外?,说听闻女儿病了,要求见圣上。但?明眼人都知圣上不会召见他。谢公自己?也?知道,却一直不走,直等?到杜家父子吃完宴席出宫……殿下,武定门不方便,换个门出宫为好。”
低语几句毕,谦恭地退下。
萧挽风淡漠道:“小公公看着眼熟,似乎御前见过。”
身穿绿袍的年轻内宦抬起头来,露出讨喜的笑容:
“有劳殿下记挂。奴婢逢春,御前殿外?伺候。”
谢明裳身子不舒坦,脑子没坏。瞥一眼前方又开始摇摇晃晃走路的河间王,心里雪亮。这厮弄得?满身都是酒,其实听他说话,人压根没醉。
如果?武定门外?揍杜家的是她爹爹,他往武定门走那才叫真正醉狠了。
前头宫道往左是西尚直门,往右是武定门。河间王果?然绕过武定门,往西尚直门走。
等?一行人慢腾腾地挪过宫门,马车已经安排好了,等?候在西尚直门外?。
送车来的正是黄内监,殷勤笑道:“巧了。咱家去寻冯公公要马车时,冯公公正好也?要寻殿下说事。冯公公叮嘱说,河间王身边似乎没有女婢服侍?殿下的亲兵怕侍奉不好谢六娘子起居,要不要调派几个宫人,跟车去府上继续照应?”
萧挽风握着缰绳踩蹬上马,道:“不必。谢六娘子有人照顾。”
“有人照顾”的谢六娘子独自在马车上颠簸。
御道街上还好,青石平整,车才转下御道街,剧烈颠簸几下,谢明裳叫停了车,下车在街边又吐了一场。
吐完她不走了。
萧挽风骑的还是那匹高?大黑马,出行未打起前后仪仗,人领着亲兵已经奔出去整条街,她非要传话把?人喊回来。不见到正主儿死活不上车。
跟车的顾沛不敢碰她。僵持一阵,当真替她传了话。
前方引路灯笼回转,十几匹轻骑风沿着街道小跑奔回。
毛色油亮的黑色骏马勒停在三步外?,骏马喷着响鼻不耐烦地踢踏,萧挽风坐在马鞍高?处,俯视路边抱膝坐着的小娘子。
谢明裳入宫折腾这一场,眼见得?比谢家撞见那日消瘦得?多了,黑而亮的眼睛倒似乎大了一圈。
谢明裳仰着头道:“我要单独和殿下说话。”
萧挽风一颔首。身边亲兵分散奔开,附近十丈之内清了场。
天色几乎全黑下去了。辽东王的谋反两个月还未平定,今年的京城比以往春夏季节萧条许多。街边叫卖的小贩早早收了铺子回家,只有远处两三间酒楼还灯火辉煌。
谢明裳坐在入夜冷清的路边,身上再妥帖的衣裳,接连吐了两场都不妥帖了。
临时备的马车里当然不会有换洗衣裳。顾沛也?没想起给她准备一套衣裳在马车里。她身上的味道和马上那位的酒气简直半斤八两。
入京五年,她还是头次遇到今天这么?荒谬的场面。
想想早晨冯喜说的那句“贵人都爱素净的,显得?人干净”,看看自己?这身“干净”,再抬头看看眼前面色看不出喜怒的“下家”,谢明裳心里升起一股古怪的想笑的感觉。
“刚才宫门外?把?杜家父子打破头的,是我父亲?”
马上的郎君不承认也?不否认,只问:“你想说什么?。”
谢明裳翘了翘唇角:“殿下,你这回被人坑了。把?我弄回家去,哪是供殿下取乐呢,分明都在等?着看殿下的乐子。我这条性命不剩多少了,丢在河间王府,我父亲必要寻殿下的晦气,两边落不了好的。”
她迎风咳了几声,好心地出主意。
“好在马车刚下御道街,转右直行,可以把?我顺路送回谢家。我在自家屋里含笑阖眼,父亲挂念你的好处,以后和殿下化干戈为玉帛,坏事也?成?了桩美谈……呕……”
这回把?刚才宫门口?喝的药酒呕了出来,全呕在衣袖上。
该说的说完了,吐也?吐完了,谢明裳坐在路边不想动弹。
暮色里晃了片刻神,她的“下家”不知何?时踩蹬下马,走近面前注视她片刻,解下披风,裹住素衣下消瘦的肩头。
她被半扶半抱地扶上马。
马主人翻身上鞍,浓烈的酒气从身后传来。她本?能地捂住口?鼻,被自己?衣袖的气味冲到,赶紧又把?袖子扯远些。
裹上来的披风倒是没什么?酒臭气,闻着有皂角洗过的干干净净的味道。
身子不舒坦的时候,舒坦是大事,其余都是小事。
比方说谢明裳擅骑马。上马后反倒比马车里少点颠簸。她顺着马儿奔跑的节奏骑坐在马背上,感觉舒坦多了。
比方说披风包裹全身,暖和避风,气味又好闻,她一路紧搂住披风不放手。
比方说身后贴上来的热烘烘的陌生男人的身躯,她只当是个热烘烘的汤婆子。
有节奏的马蹄声里,谢明裳身子往前,枕着披风,熟谙地搂着马脖子,不知不觉竟眯了一会儿。
闭眼眯觉的时辰应该很短。再醒来时,骏马还在长街上缓行,长街尽头转向,前方出现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宅子。
她此刻以侧躺着的姿势,不伦不类地横在马背上。
从下往上看人的角度很少有好看的,萧挽风下颌骨的弧度凌厉,从她的角度看,居然不难看。